
走過莫拉克風災
2009年8月8日,莫拉克颱風挾帶風雨襲台,巨大降雨量釀成嚴重災情,洪水肆虐造成道路中斷,更重創山林,許多部落地區遭到吞沒,原民被迫離開家鄉。災後重建是一條漫漫長路,但在不懈努力與各界協助之下終於逐漸站穩腳步。精選5篇文章,一起來看屏東霧台山中居民,如何重返母親懷抱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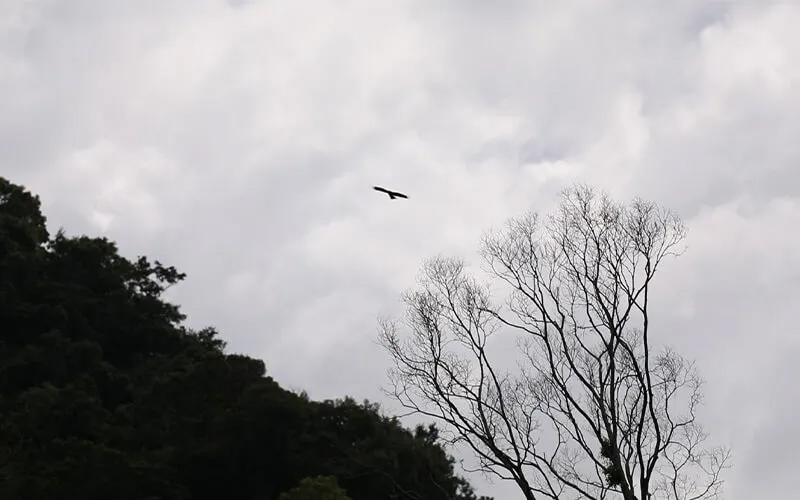
前往屏東霧台的路上,有機會可以看見黑鳶。
「你看過五色鳥群棲息在整棵樹上嗎?我看過……。」
「你看過熊鷹展翅飛翔嗎?我看過……。」
「季節對的時候,在一路蜿蜒往山林的台24線上,我還曾多次與黑鳶同行,每一次去都像是去尋找曾經擁有的東西,彷彿等一下就會有熟悉的老人家從山裡回來。」
說起霧台,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教授陳美惠對當地的自然與人文有著特別的眷戀,十五年了,她不記得進出霧台多少回了,看過最美麗的霧台,也看過莫拉克災後最悲慘的霧台,但她從不曾有過一絲絲猶豫,即使在搭乘流籠過河的那一瞬間,她也沒想過撤退。
從九二一到莫拉克
「可能我自己曾從瓦礫堆中爬回來,所以我知道只要人活著,就沒什麼好怕的。」九二一地震那年,她在南投鳳凰谷鳥園工作,地震當晚她慌張地從宿舍逃了出來,卻因為再度陪友人回去拿東西,而受困瓦礫堆中,當時她已懷有七個月的身孕。
她一度以為死亡很近很近了,還好她躲的地方還有一絲空間,翌日清晨,看到陽光照進瓦礫堆,她和友人終能脫困,她便知道「只要人活著,一切都有可能」;或許這一幕太深刻,陳美惠說起這些過往,堅定的語氣裡並沒有太多情緒,也或許對生命的靭性早有體悟,在莫拉克之後,即使當時的霧台鄉已是柔腸寸斷,她仍堅信魯凱族人終能挺過。
陳美惠是台南人,離開鳳凰谷鳥園後,她轉往當時的文建會學習社區營造,後來又轉到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原林務局),因緣際會,社區與林業的概念在她的腦海裡一路整合靠攏;2006年她把焦點轉回屏東,從墾丁的社頂開始協助部落拓展生態旅遊,也是從屏東開始,如何實踐社區林業有了清楚的面貌。
社區林業
社區林業(community forestry)是林業經營的新趨勢,其經營理念更強調社區參與,公私共管與共享;陳美惠進一步說,所謂的社區林業是以保育為核心,力邀社區參與,透過公私協力共管,最後帶來的經濟及社會價值並可與社區共享。
至於在各社區推動的生態旅遊,陳美惠說,生態旅遊並非社區林業的目的,而是達成社區林業的重要策略,社區藉此參與資源調查、環境維護及遊程規劃,因為了解森林,而更愛森林,而不是像過去主打保育的作法,反而與鄰近社區產生了對立,甚至社區人必須遠走他鄉才能生活,這樣的保育反而狹獈了。
2002年她把社區林業的概念寫成計畫,同一年,台灣也剛好喊出生態旅遊元年,陳美惠記得那段時間每次下鄉拜訪時,每個社區幾乎都在談生態旅遊,其實最終的目標還是社區林業。

原來在風災以前,就打算在阿禮部落經營以生態旅遊為策略的社區林業模式。
2008年在前屏東縣長曹啟鴻的牽線下,她前往霧台鄉的阿禮部落,便是以生態旅遊為起手式,當時如魔鬼般的莫拉克尚未發生,阿禮也一如位於雲霧中的山中古國,一個以生態旅遊為策略的社區林業模式就要在阿禮施展手腳,沒有想到萬事俱備後,2009年的8月卻遇上了莫拉克颱風,山崩地裂、洪水肆虐,不但路沒了,連山林部落都幾乎被吞沒。
災後,當時的政府考慮的當然是儘快安置災民,甚至鼓吹部落安全堪慮的災民放棄山林,不過陳美惠第一時間想的是,愈是斷壁殘垣、愈是沒有人管的森林,那才是盜獵盜伐的溫床;於是她向當時的林務局(已更名為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申請災後環境監測計畫,讓選擇留在部落、僅存的四戶人家協助監測災後的森林變化。
「社區參與、公私協力原本就是社區林業的宗旨,尤其在災後實施更具意義。」陳美惠相信:「那是一種信心的加持,阿禮有人,就不是沒人管的部落,只要有人,就會留下種籽。」一位長期陪伴的學者如此堅定,反而鼓勵了所有選擇留在山林的人,儘管不確定前方的路到底要多崎嶇。

阿禮部落。(攝影:陳建豪)
搭流籠走河床
霧台鄉是屏東縣唯一的魯凱族鄉,全鄉人口僅三千多人,莫拉克颱風之後,除了霧台村、大武村、部分佳暮村民及少數阿禮村民外,其餘均遷往山下,當時全鄉四分五裂,還有山上山下之分,加上永久屋尚未完成,他們只能暫時被安置在不同的安置中心,家在哪裡?是每一災區心中深深的疑惑。
但是陳美惠的腳步並未停歇,她幾乎跑遍了每個安置中心,而留在山上的大武村為了尋找生機,也開始找陳美惠討論,受傷的山川尚未修復,由陳美惠領軍的屏科大團隊已開始動了起來。

直到谷川大橋通車後帶動人流,才有更多人願意回到神山和霧台部落。
「上山的路與災民的心一樣破碎,這是災後的兩大難題。」當時到屏科大唸研究所的廖晋翊經常跟著老師上山下山,他發現那時災民的心是被撕裂的,想放棄山林又怕失去山林,想上山又怕難以抵擋天災,還有財產及土地的分配等等現實問題,每一次的討論都會有各種不同的人提出各種主張。
從台中來的他並沒有被柔腸寸斷的路況嚇跑,倒是有好幾次被人的問題「震憾到」,「所幸一切都過了。」外號「熊大」的廖晋翊依然笑得靦腆,幾年的訓練下來,他和陳美惠老師一樣,韌性的心愈來愈堅強。
通往霧台鄉的谷川大橋是於2013年完工,那是災後的第四年,在那段災後的復原期間,陳美惠和所有的村民一樣,進出大武部落仍得走河床、搭流籠,她記得有幾次的夜裡自己還在河床迷了路,幸虧族人協助才脫困,但是這些絲毫不曾動搖過她的行動,在群山包圍的河谷,她和魯凱族人看過相同的天空、跨過一樣的洪流,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陳美惠更能體會村民想要留在部落拯救家園的心。
森林人的心
災後,陳美惠開始帶著部落實踐里山根經濟,養蜂、養雞、種植山當歸、金線連,一樣樣產業在阿禮及大武部落陸續開花結果,山林生物的多樣性與在地知識的整合,再次以里山根經濟的模式呈現,大武部落利用農地養出的大武森雞,更是混農林業的實踐。
「山不轉,路轉。」從莫拉克至里山根經濟的實踐,霧台鄉走了十多年,雖然時間很長,但陳美惠總是說「走得慢,不擔心,人回來很重要,社區行動力也很重要。」

最一開始養雞,是為了部落儲備糧食,提升備災的能力。
她舉阿禮部落為例,如今再重回阿禮,除了人少一點外,部落其實沒什麼改變,依然看起來幽幽靜靜、乾淨乾淨,「這樣的維護力正是因為當初族人的不放棄。」而當初選擇留在山上的大武部落,走過山崩地裂,如今產業與社區早已又回到那個生氣勃勃的大武了。
至於當初跟著陳美惠老師進出森林的「熊大」廖晋翊,在研究所畢業後竟也選擇留在山林,和魯凱族人一起打拚,2018年他還成立了源森生態公司,從養蜂開始拓展林下經濟的六級化產業。

「熊大」廖晋翊。
「我從一個養蜂人的角度來看霧台,那真是一個特別的地方,從海拔六百公尺到一千兩百公尺之間,在很短的距離內,蜜源卻十足的多樣性。」廖晋翊說,不管是龍眼蜜、荔枝蜜或是百花蜜,霧台的蜜蜂從不讓人失望,而且各部落的味道也不盡相同;他曾在同一年的五月,同時蒐集阿禮蜜、佳暮蜜及吉露蜜,沒想到三地的味道完全不同,有的會辣、有的會苦,有的還有花香的甜味,「如此多樣,正是霧台對我的吸引力。」
家住台中的他,高職讀的是森林科系,雖然對森林知識並不陌生,但從沒有想過離家到屏東科技大學就讀研究所,竟會從此改變自己的一生,不但真的留在了森林,並成為真正的森林養蜂人。
從打開蜂箱,觀察蜜蜂的動靜或帶著蜂箱到山裡牧蜂,已完全難不倒這位都市來的青年,「雖然被蜜蜂叮咬的地方是痛的、是紅腫的,但是果實是甜蜜的,是獨一無二的。」

他說,霧台除了環境吸引他外,另一個吸引他的原因是霧台的人;雖然在莫拉克災後,因為人的緣故,一度衍生不少紛擾,但在廖晋翊的心中,魯凱族人是敦厚的,雖然他們也稱廖為「白浪」(部分原住民族對漢人的稱呼),但一旦建立了互信,他們便會以真誠的方式與人相處,從災後迄今,留在部落努力的人早已建立了革命情感,「是他們讓我離不開霧台。」
不記得進出霧台多少次了,想起霧台的天空、霧台的山林,廖晋翊很篤定地說:「不必把我歸類為霧台哪一個部落的人,我早已在霧台裡面了。」
*本文來源:《與黑鳶同行的人─我在霧臺》,教育部USR計畫「里山根經濟-林下經濟、生態旅遊的軸帶深耕與農林地碳匯人才培育」,統籌企劃:陳美惠,文字:翁禎霞。
網站連結: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7344
